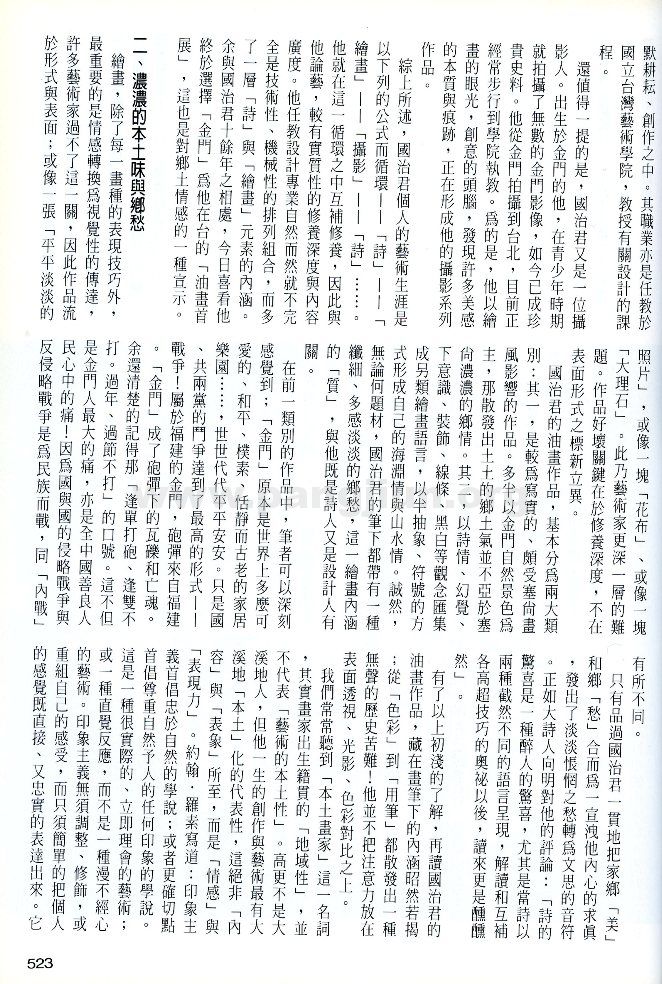CLOSE
CLOSE
張國治君與余在國立台灣藝術學院共事至今,已有十二春秋,我們藝術亦有十二個年頭,是藝術朋友。藝術家與藝術家的往來,有時是好友但不一定是「藝術朋友」,因為畫家的創作是獨立的,多半閉門揮灑,不善論藝,彼此無深入機會相交談。然,國治兄是善思考、是博學而能深論之君。這同他在高中時代還是青少年就十分敏銳、多感、擅寫詩、文思豐富,是位早熟的詩才有關。
國治君在詩壇的成就大於繪畫,他已發表千餘首詩,出版詩集、散文九冊,頗受台灣詩壇與國際文學界好評。但是,他仍然是一位繪畫人,科班學習設計與繪畫,不但偏愛油畫,而且始終在默默耕耘、創作之中。其職業亦是任教於國立台灣藝術學院,教授有關設計的課程。
還值得一提的是,國治君又是一位攝影人。出生於金門的他,在青少年時期就拍攝了無數的金門影像,如今已成珍貴史料。他從金門拍攝到台北,目前正經常步行到學院執教。為的是,他繪畫的眼光,創意的頭腦,發現許多美感的本質與痕跡,正在形成他的攝影系列作品。
綜上所述,國治君個人的藝術生涯是以下列的公式而循環──「詩」──「繪畫」 ──「攝影」──「詩」……。他就在這一循環之中互補修養,因此與他論藝,較有實質性的修養深度與內容廣度。他任教設計專業自然而然就不完全是技術性、機械性的排列組合,而多了一層「詩」與「繪畫」元素的內涵。余與國治君十餘年之相處,今日喜看他終於選擇「金門」為他在台的「油畫首展」,這也是對鄉土情感的一種宣示。
繪畫,除了每一畫種的表現技巧外,最重要的是情感轉換為視覺性的傳達,許多藝術家過不了這一關,因此作品流於形式與表面;或像一張「平平淡淡的照片」,或像一塊「花布」、或像一塊「大理石」。此乃藝術家更深一層的難題。作品好壞關鍵在於修養深度,不在表面形式之標新立異。
國治君的油畫作品,基本分為兩大類別:其一,是較為寫實的、頗受塞尚畫風影響的作品。多牛以金門自然景色為主,那散發出土土的鄉土氣並不亞於塞尚濃濃的鄉情。其二,以詩情、幻覺、下意識、裝飾、線條、黑白等觀念匯集成另類繪畫語言,以半抽象、符號的方式形成自己的海淵情與山水情。誠然,無論何題材,國治君的筆下都帶有一種纖細、多感淡淡的鄉愁,這一繪畫內涵的「質」,與他既是詩人又是設計人有關。
在前一類別的作品中,筆者可以深刻感覺到;「金門」原本是世界上多麼可愛的、和平、樸素、恬靜而古老的家居樂園……,世世代代平平安安。只是國、共兩黨的鬥爭達到了最高的形式——戰爭!屬於福建的金門,砲彈來自福建。「金門」成了砲彈下的瓦礫和亡魂。余還清楚的記得那「逢單打砲、逢雙不打。過年、過節不打」的口號。這不但是金門人最大的痛,亦是全中國善良人民心中的痛!因為國與國的侵略戰爭與反侵略戰爭是為民族而戰,同「內戰」有所不同。
只有品過國治君一貫地把家鄉「美」和鄉「愁」合而為一宣洩他內心的求真,發出了淡淡悵惘之愁轉為文思的音符。正如大詩人向明對他的評論:「詩的驚喜是一種醉人的驚喜,尤其是當詩以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呈現,解讀和互補各高超技巧的奧祕以後,讀來更是醺醺然」。
有了以上初淺的了解,再讀國治君的油畫作品,藏在畫筆下的內涵昭然若揭;從「色彩」到「用筆」都散發出一種無聲的歷史苦難!他並不把注意力放在表面透視、光影、色彩對比之上。
我們常常聽到「本土畫家」這一名詞,其實畫家出生籍貫的「地域性」,並不代表「藝術的本土性」。高更不是大溪地人,但他一生的創作與藝術最有大溪地「本土」化的代表性,這絕非「內容」與「表象」所至,而是「情感」與「表現力」。約翰‧羅素寫道:印象主義首倡忠於自然的學說;或者更確切點首倡尊重自然予人的任何印象的學說。這是一種很實際的、立即理會的藝術:或一種直覺反應,而不是一種漫不經心的藝術。印象主義無須調整、修飾,重組自己的感受,而只須簡單的把個人的感覺既直接、又忠實的表達出來。它同時也是一種公正無私的藝術;個人的感情在印象主義裡沒有地位,就算一件印象派力作予人強烈的感動,也只被視為一種一時的眩惑而已。當米勒畫農夫在田裡拾穗時,當梵谷畫他自己的靴子時,何嘗不含有一絲向社會抗辯的意味?莫內也曾有過困苦的日子,但從他的作品裡,卻一點也感受不出。事實上,任何一種對生活狀況持續的不滿或批評,都與印象主義的原則相違,因為印象主義根據定義,是一種隨想寫實藝術。
高更則別有野心。他相信,善用自然而非在它面前卑躬屈膝,是藝術家的責任。從以上的討論,再反觀以上所提及的國治君作品,他是強調了「結構」的「力」,以較單純的色調突顯個人在大時代背景下的情感。
國治君的另一類作品是完全不同的,以近作為多。他從無意識的隨意中去發現、提煉有形的詩,此分創作境界之昇華。中國的藝術哲學,自古非常講究「無意得天趣」、「不法之法」。但這一最高境界之前提,就是「筆墨功力」、「思想」、「多方修養」。西方的繪畫亦是在探索類似的道路。除色彩表現力、筆觸肌理外,線與非表象之造形、平面化的張力與空間,畫家往往會被形式表象所騙,例如只畫「光影」和「表象」的精確。但是,當能力不及時,又會走向另一個反面,即「為形式而形式」──仍然是一種空洞的、沒有內涵的,甚至完全沒有基礎的(包括有繪畫技巧修養)之「形式」,即所謂江南方言的「煞有介事」。
國治君近年的作品是半抽象、符號的。以山川、大海自然現象以及生理現象的心靈觀感為創作源泉。從小在金門島長大的他,對海的情感是毋庸置疑的,海的神秘、人與海的互依互類都是他腦海中的「詩」與「情」,他偏愛深藍色和深藍綠。以余淺見,油畫統一的深藍色,技巧是很難發揮的,肌理的變化不易突顯,但作者卻以透明油畫色反覆重疊與「乾擦」,效果別是一般。
作品〈船堡〉,與其說是一幅平面的「變形畫」,不如說它是一幅「有形詩」,它的線條、造形富有詩的韻味,好似夜空停泊的漁船;亦好似浮出深海的珊瑚礁;又似月色下的海市蜃樓,有太多的想像空間供觀者發揮。但余的感覺,總有一種盤根錯結的哀傷!但不必「解套」,人生本來如此……。
作品〈星夜曳航〉就比前者輕鬆多了,帶有童貞的幻覺、造形、線條都很優美。色彩在強烈的對比中,富濃厚裝飾性。分解造形再次組合構成,在似與不似之間,呈現新的視覺影像。此幅作品 的底色處理得很好,有粗布「蠟染」和「磨漆」趣味。
作品〈意象的海洋〉是一幅運動形式的構成圖象,看來像深海中大大小小的「花魚」,但並不重要。海洋中的生命與活力才是主體。一種似乎海洋重力消失的景象;那圓形和半圓形的符號自由地擺盪,顯現一種純粹的運動形式,但巨大的生物(一條大魚)以漸強的引力把小生物束縛在它的四周,沒有像宇宙太空那麼自由自在。也許在平面抽象的裝飾感中,圖騰最後仍然無法擺脫自然規律的存在。
作品〈山水誌系列之(六)〉是一幅佳作。作者已經擺脫了描繪山水景色之表象,擴大了「局部」造形,非常簡化地突顯了自然的永恒,他吸收了中國水墨畫、黃賓虹、李可染的「惜水如金」的方法,即「留白」很少,白色線條穿梭在深藍色不同明度的方塊之中,透明色留下了自然的紋理與筆觸。以山而論,他並非畫「台灣山」或「大陸山」,而是文人心目中的山水情,更具永恒的藝術價值。
而努力國治君的油畫作品,初視之,並不是那麼色彩絢爛有震撼之力,而是需要細 細品味的「有形詩」,他同時是一位詩人,畫作自然以中國人文人情懷為主軸。他又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有設計修養和攝影修養的人,他的藝術成長當然脫離不了他的生活根基,絕不像不少畫家始終茫茫然地跟隨西方畫風而失自主力。
藝術的「民族性」與「本土性」。是許多學者常言的話題,但對畫家而言,絕非畫了一間「土房子」與「厝」就具備了「本土性」。感情才是重要的。國治君太愛他的金門之鄉,無論他所畫的房屋、街道、海、船、魚等都散發出一種予取予求的非常自然的鄉土味,實屬難能可貴。此乃台灣藝術發展必走的藝術之路。
筆者既非「理論家」更非「評論家」。余是沒有資格和能力詮釋張國治的油畫藝術,只因囑我隨筆,斗膽撰文,甚感歉意。在此衷心地祝賀國治君在金門的首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