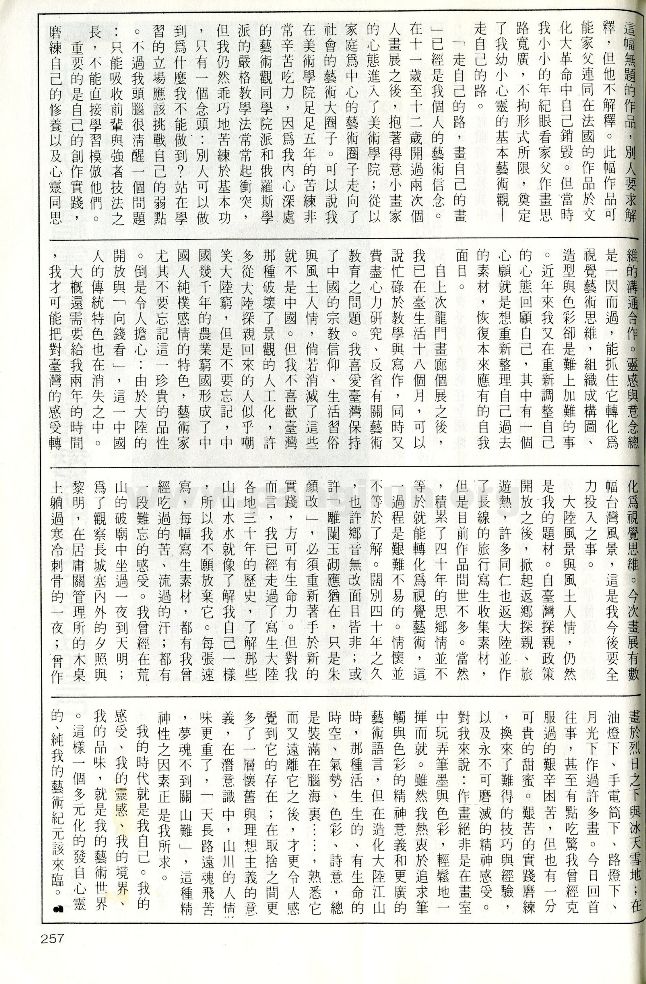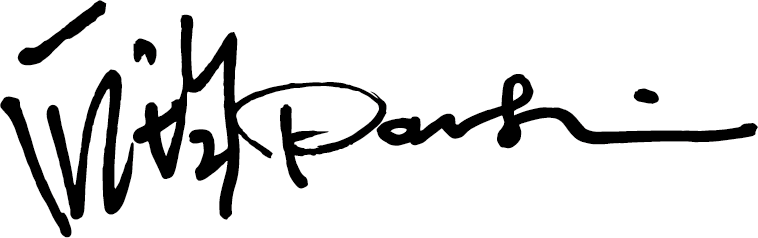 CLOSE
CLOSE
自我十一歲首次公開個展至今,已進入第四十二年藝術生涯。漫長的四十餘年又似乎只是昨日一閃而過。我從來不對自己作任何肯定與否定,人生本來不可能功德圓滿也絕非毫無價值。我在抗日戰爭中成長,經歷了戰亂。在當年的亞洲第一大城市──上海經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轉變。大學畢業於古老的京都──北京,經歷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知識份子經受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打擊與排斥的考驗。經歷了在香港七年有餘的自由生活後,感受到對文化藝術的虚假、冷漠與欺騙。一年半前我又開始了生活在臺灣的藝術生涯………。雖然我從未感到藝術創作辛勞的疲倦,但我和許多人一樣,內心深處感到中國人的災難、艱辛與不幸……,歷史的經驗證明:任何權勢、政治、社會,都有它的歷史階段性、暫時性和不足性。在複雜的歷史長河中,唯有幾千年的文化藝術匯集而成的中華民族的精神性是永恆的。因此我面向自然;面向最普通、最平凡然而是人類中較為純美的人;以及那些與人共存的一花一草、一磚一瓦,從他們中間去探求本來面目的美。
四十年前,我十歲左右,家住在廣州光孝寺內,當時是廣東國立藝專的所在地,家父是美術系系主任,馬思聰是音樂系系主任。寺院內除廟殿外,有一棵千年古老的大菩提樹,我整天在院內跑來跑去,開始畫油畫寫生,畫風都受了野獸派的影響。有一次我眼看一位藝專學生畫了一幅女人體向家父請教,他的畫法就是學習馬諦斯,但用生硬的黑色粗線勾出人體,這位學生被父親大罵一頓,家父告誠他:「你學別人畫畫一輩子畫不好畫,你是不懂,亂學、亂畫。」那位學生走後我對家父說:「他是學丁衍庸校長。丁衍庸的油畫就這麼畫。」家父没有正面回答,只說:「馬諦斯只有一個没有第二個。」這件事對我刺激很大,我想還是家父說得對,即使學馬諦斯、畢卡索,學得亂了真也没有用,別人還是承認真的馬諦斯、畢卡索,學人家没有出息。再想想:家父當年在巴黎已結交馬諦斯、畢卡索,但他的畫風是那麼不同,他在抗戰期間,甚至畫了不少苗族生活與唐人舞蹈,與西方毫無關係。生活在廣州藝專的年代,我看家父畫了一幅非古典寫實的油畫靜物,但同時他又畫了兩幅超現實的作品,其中一幅,印象中畫的是一隻又非常真實的手,同時又有一隻用黑顏色印上去的黑手……,這幅無題的作品,別人要求解釋,但他不解釋。此幅作品可能家父連同在法國的作品於文化大革命中自己銷毀。但當時我小小的年紀眼看家父作畫思路寬廣,不拘形式所限,奠定了我幼小心靈的基本藝術觀──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畫自己的畫」已經是我個人的藝術信念。在十一歲至十二歲開過兩次個人畫展之後,抱著得意小畫家的心態進入了美術學院;從以家庭為中心的藝術圈子走向了社會的藝術大圈子。可以說我在美術學院足足五年的苦練非常辛苦吃力,因為我內心深處的藝術觀同學院派和俄羅斯學派的嚴格教學法常常起衝突,但我仍然乖巧地苦練於基本功,只有一個念頭:別人可以做到為什麼我不能做到?站在學習的立場應該挑戰自己的。不過我頭腦很清醒一個問題:只能吸收前輩與強者技法之長,不能直接學習模倣他們。
重要的是自己的創作實踐,磨練自己的修養以及心爱同思維的溝通合作。靈感與意念總是一閃而過,能抓住它轉化為視覺藝術思維,組織成構圖、造型與色彩卻是難上加難的事。近年來我又在重新調整自己的心態回顧自己,其中有一個心願就是想重新整理自己過去的素材,恢復本來應有的自我面目。
自上次龍門畫廊個展之後,我已在臺生活十八個月,可以說忙碌於教學與寫作,同時又費盡心力研究、反省有關藝術教育之問題。我喜愛臺灣保持了中國的宗教信仰、生活習俗與風土人情,倘若消滅了這些就不是中國。但我不喜歡臺灣那種破壞了景觀的人工化,許多從大陸探親回來的人似乎嘲笑大陸窮,但是不要忘記,中國幾千年的農業窮國形成了中國人純樸感情的特色,藝術家尤其不要忘記這一珍貴的品性。倒是令人擔心:由於大陸的開放與「向錢看」,這一中國人的傳統特色也在消失之中。
大概還需要給我兩年的時間,我才可能把對臺灣的感受轉化為視覺思維。今次畫展有數幅台灣風景,這是我今後要全力投入之事。
大陸風景與風土人情,仍然是我的題材。自臺灣探親政策開放之後,掀起返鄉探親、旅遊熱,許多同仁也返大陸並作了長線的旅行寫生收集素材,但是目前作品問世不多。當然,積累了四十年的思鄉情並不等於就能轉化為視覺藝術,這一過程是艱難不易的。情懷並不等於了解。闊別四十年之久,也許鄉音無改面目皆非;或許「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必須重新著手於新的實踐,方可有生命力。但對我而言,我已經走過了寫生大陸各地三十年的歷史,了解那些山山水水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樣,所以我不願放棄它。每張速寫,每幅寫生素材,都有我曾經吃過的苦、流過的汗;都有一段難忘的感受。我曾經在荒山的破廟中坐過一夜到天明;為了觀察長城塞內外的夕照與黎明,在居庸關管理所的木桌上躺過寒冷刺骨的一夜;曾作畫於烈日之下與冰天雪地;在油燈下、手電筒下、路燈下、月光下作過許多畫。今日回首往事,甚至有點吃驚我曾經克服過的艱辛困苦,但也有一分可貴的甜蜜。艱苦的實踐磨練換來了難得的技巧與經驗,以及永不可磨滅的精神感受。對我來說:作畫絕非是在畫室中玩弄筆墨與色彩,輕鬆地一揮而就。雖然我熱衷於追求筆觸與色彩的精神意義和更廣的藝術語言,但在造化大陸江山時,那種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時空、氣勢、色彩、詩意,總是裝滿在腦海裏……,熟悉它而又遠離它之後,才更令人感覺到它的存在;在取捨之間多了一層懷舊與理想主義的意義,在潛意識中,山川的人味更重了,「天長路遠魂飛,夢魂不到關山難」,這種神性之因素正是我所求。
我的時代就是我自己。我的感受、我的靈感、我的境界、我的品味,就是我的藝術世界。這樣一個多元化的發自心靈的、純我的藝術紀元該來臨。